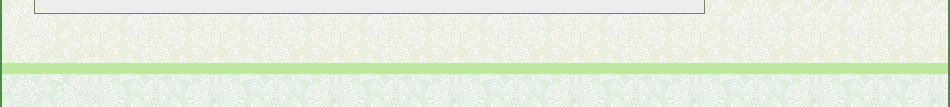寻香
——我的川剧碟变之一
文/阿依卓
我国藏族人民流行这么一句话:“有缘人犹如鸟同石块在路上相遇”,意思是说,一只鸟落在哪一块石头上,不是山鸟的计划,而是天缘,用来比喻人与人之间的相遇完全是靠上天的缘分。
成都是川剧主要的发祥地,在旧社会川剧艺术是当地人生活主要的娱乐方式,当时的人们稍有空闲,不论是达官贵人,还是下里巴人,没有人不讴几句川剧唱腔的;随着社会的演变,各种艺术表现形式及娱乐节目层出不穷,川剧与当代观众的疏离是不可回避的客观事实,但它作为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还是要继续传承下去的。
我与川剧的结缘,始于以旋律为傲,号称蓉城舒伯特的老公,他利用在文联就职之便,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晴天,让我结识了川剧大师邓先树之子邓翔先生。
初见邓老(现实版的邓翔先生并不老,邓老是我对他的尊称哈,嘻嘻),感觉眼前这位邓老简直不是人,而是“妖”是“魔”,否则,他怎会对古今诗词歌赋、戏曲等领域熟悉得一塌糊涂。于是乎,我心底的自卑和虚荣心在邓老面前,无法控制地迅速漫延;抱着:总有一天我也要像邓老那样成“妖”成“魔”,并能得到众“妖”众“魔”的夸讲。于是,我穿过邓老敲响了邓老的父亲邓先树嫡传弟子赖华芬老师的家门……。
其实,早在敲响赖华芳老师家门前,我便开始四处宣扬:“我正跟随邓先树先生的嫡传弟子学习川剧,好家伙,这可是大师啊,我传承的都是民族的精华,我正在无私地拯救咱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。”看着被我洗脑的人们用崇敬的眼光看着我,心情简直就是倍儿爽。
踏进赖华芬老师的家门,第一感觉是,又见“妖”见“魔”了,赖华芬老师身材窈窕、美目盼兮、巧笑倩兮,川剧的儒雅贯穿每个骨节与细胞;如此气质佳人,你相信她已经有71岁了吗?于是,我又自作聪明地尊称赖华芬老师为“姐姐”。
“姐姐”6岁进群生川剧团学习,由于“姐姐”勤奋好学,很快在众多学员中脱颖而出,团里便着重培养,并支持在外进修;因此,“姐姐”便博采当时众多大师的优点,如邓先树、董绍舒(玉婷婷)、琼莲芳等,因邻里之故,主要师从邓先树先生,邓先树先生注重口传心授,教学非常严谨,每学一出戏,他都要细致分析其中的社会背景和人物的生活含义,讲解在特定时间、环境中剧中人物的联系和心理冲突;并要求把剧中人物台词、表演全部学会,这样在舞台上与别人才能配合默契。“姐姐”说:“邓先树先生特别爱学习,他注重吸取姊妹艺术的优点,灵活运用到川剧艺术的表演之中。”无需置疑,“姐姐”继承了邓先树先生的尽业和好学精神,只是作为“姐姐”学生的我,其惨状是不言而喻的。
瞧,第一节课,便是严格的考试。
好的是,我从小热爱舞蹈,虽没经过专业训练,兴趣使我的舞蹈水平至少在业余之上,再说,我大小还是民间“投缘文化艺术团”的团长,不就是考考我的基本功吗,哼,小菜一碟,相信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;果不其然,一曲《吉祥孔雀》顺利通过了“姐姐”对我设制的形体考核。
上课了,我认真而新奇地看着“姐姐”古典、优雅、漂亮的出场亮相、横8字圆场,水袖飘飘,我沉浸在一种心醉的快乐中,感觉自己打开了一座宝藏,目不暇接,浑身酥麻,心中那颗戏曲小树,吐出绿叶,花开满枝。我满心都是欢喜、都是清香,急不可待地将所学用于“投缘文化艺术团”的舞蹈创作中,试图用行动传承和发扬心中的戏曲艺术,试图让大家分享我内心的快乐。
兴奋之余,殊不知,“姐姐”是故意让我体会到学习川剧的快乐,真正的“好戏”还在后头呢!